|
金子又闪光了(十四) 凉州散记之十四-------五七干校(转载)
刚到农机所不久,该夏收了。
文化革命以来,干部和劳动已结下了密不可分的“友情”。尽管是堂堂国家机关,每年一到七月,和农村一样,也进入了自己的夏收大忙季节。哦,那儿种的是春小麦,三月耘籽,七月收获。 那时候,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,各机关都有自己的农场,不用交公粮,收入全归己。好事啊。各单位办农场的积极性都很高。我们局也有自己的农场,种的春小麦和胡麻,还养了几口猪。每年过年前分东西时最欢乐了。今天分猪肉,明天往家里扛精白面,后天提清油,不要钱,何乐而不为?人人笑容满面,像农民丰收,今年又能过上个肥年了。但是,好吃的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春天种麦,夏天割麦,冬天磨面,都得人去干。一年三次,没个跑,常有我。 地区生产指挥部,过去叫专员公署,他们的农场大,种的麦子多,可缺人干活。领导机关嘛,自有它的办法。发文下通知,让下属局级单位抽人干,当然是无偿了,就和服劳役一样。今年局里让我去了。 各种劳动里,夏收最辛苦。向来被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视为畏途。又热又晒又累。哪像坐办公室,扇子一挥,小茶一喝,要舒服有多舒服。我是新来的,又最年轻,王老五一个,没拖累,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?带上行李,我去也。 地区生产指挥部的农场在武威东南处,一个荒滩上。是地区机关的生产基地,许多单位的农场也在这儿。它还有个名字,叫五七干校。离黄羊镇不远,大,很广阔。方圆几十里,没有路,没有树,没有河流,没有草地,除了荒滩还是荒滩。倒是和我呆过的解放军农场却有几分相像。 我们局的农场也在这里,就在干校后面不远。一个小院落围住了一排房子,耕地就在周围,也有挺大一块。我还不知道,以后那是我的常去之处。 这一次夏收,我们不是五七干校的学员,不归干校领导,住在干校的校舍里,给生产指挥部干活,在他们的食堂吃饭。干校的教员干部对我们比较客气。 我没来过干校,什么都觉得新鲜。 还没开始干活,局里的老刘领着我在干校里转悠。干校大名在外,其实也就是几排平房,土墙,没粉刷,也没围墙。 老刘告诉我:“那是现在了。过去一说上干校,就害怕得打哆嗦。上干校就是搞运动。不是斗人就是挨斗,一进干校心就提着。那个时候……”老刘感叹不已。我早听说了,70年前后,一说进五七干校办学习班,实际上就是挨斗和斗人。倒霉的人,有问题的人,进五七干校不亚于过鬼门关。 路上碰见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,中等个子,陕西口音,胖乎乎的,圆脸。不管碰上了谁都会奉上一个谄媚的笑容,说几句应景的好话。我奇怪,这人怎么这副德行啊,见谁拍谁的马屁,至于吗?文化革命已七年多,人们看穿了许多事,经得多了,见得广了。谁怕谁? 老刘是老干校了,常来,什么都知道。他压低声音告诉我:“那人姓王。过去是造反派,干校的实权人物,可不得了的人。干校的第一把手是地区革委会主任兼着,每期学习班只在开学时来一次,露露脸就走了。平时,大权全在这个人手里攥着。他说斗谁就斗谁,说整谁就整谁,威风着呢。没想到突然倒大霉了。” 我好奇地问出了什么事。老刘接着说,“有一天,要斗反革命了。要斗人了。大会场坐满了人,没人说话,都紧张,不知道今天姓王的要收拾谁了。 开会了。姓王的主持今天的批斗大会。他头戴军帽,臂戴红卫兵的大红袖章,很神气地站在主席台上。开始了。他嗓门大,有派头。拿了张纸头,扫一眼,就大喊把李××揪出来,把张××揪出来……气势汹汹,不可一世。挨斗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到台上,低头撅腚,站了一大排。 开始大批判了。姓张的会掌握大会气氛,把革命的火越烧越旺。他不断领呼口号,全场上下情绪高亢,革命热情一浪高过一浪。姓王的一看,好,再加上一把火。他领头举手高呼:“打倒毛主席!保卫刘少奇!”话音一出,全场一下子静得没有一丝儿声音了,就象一切都停滞了,用电影的行话说是——定格了。那人一楞,马上知道出大事儿了,坏了,口号喊反了。一刹那间,只是仅仅一刹那间,马上全场掀起了扑天盖地的狂潮。‘王××攻击毛主席,罪该万死!’‘打倒王××!’ ‘打!打狗日的!猛打!’不用领导吩咐,马上有几个人跑上台去,一把把他的红袖章捋下来,旧军帽扔了,胳膊被弯向后面,头被压向地面,直接拖到外面的煤堆上,狠狠打了起来。想表现积极的、想取而代之的、恨他的、被他整过的、将被他整的、凑热闹的、公报私仇的、惟恐天下不乱的,一窝蜂拥了上去,七手八脚打了起来,立马把他打了个半死,要不是有解放军在场保护,他活不到今天。”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。萧墙之祸,危在旦夕。这就是无奇不有的文化大革命。台上和台下离得并不远。 武威的夏天,干旱少雨,宜于夏收,绝无龙口夺食之虞。但灾害同样有,叫干热风。如果小麦灌浆期遭遇了干热风,几天热风一刮,麦穗看起来粗大,但瘪瘪的,照样颗粒无收。干热风,防不胜防。碰上了,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还好,今年风调雨顺,看来是个大丰收。 开始割麦了。那是我最头痛的事。且不说天上有骄阳烤炙,脚下有土地潮气熏蒸;也不说腰疼得直不起来,大汗淋淋也顾不上擦;更不说手已磨破,包手的手绢上血迹淋淋;就只说那人得像个机器一样:左手拦过来麦棵,右手挥刀割下,再轻轻放在地下;左手拦,右手割,放下……就这单调的动作,不断重复,不停不息。麦垅长得看不到头。一干就是半天,一干就是一天……这样的活折磨人的神经。我整整干了两个星期,活脱一层皮。好在我年轻,顶下来了。 我是从戈壁走出来的人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(待续) 几千万受过“十七年旧教育制度”毒害的娃们,来到了广阔天地,接受二十年前土改时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并且还要扎根。太豪迈了! 豆蔻年华的女娃,来到了大草原,脸晒黑了,身体健壮了,心更红了。 在我“早期革命实践” ,接受再教育的窑洞前来了一张。后来,提着糕点、水果去感谢教育者,并赔礼道歉,说当时没有好好接受再教育。可当年的小队长却说:“当时,你们正处在长身体,学知识的阶段,能来和我们一起就着盐腌的红薯杆子、吃喝包谷碴子,住窑洞已经很不错了,那么重的农活你们干不了的,硬干就把身体累垮了,你还能长那么高吗?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。” 这就是那“二牛抬杠”的农耕方式,和一千七百多年前北魏壁画上的几乎一模一样,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在沿用。比西周时代的进步仅在于用畜力代替了那“千耦其耘”人力刨地。满世界都已经靠科学在致富了,可在河西地区依然还在靠畜力和人力填饱肚子。 现在好了,紧跟了时代的步伐,从耕耘到收获都已经实现机械化了。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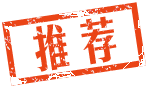
 /1
/1 